新闻自由的扩大与新闻效能的衰减

文/李蒙
在11月28日的“艺术独立论坛(AIF)对话”第五期:《漫漫上访路——关于信访问题的中国报告》活动中,在于建嵘、贺卫方、张鉴墙三位老师的对话讲座中,我即席发表了一分钟的讲话,其中提到新闻自由的扩大与新闻效能的衰减,是围绕上访问题来谈的。(关于这次讲座还写了另外一篇文章:《上访群体的利害算计——向贺卫方老师请教》)
首先的话题:中国的新闻自由是在不断扩大,还是在日趋缩减?
以我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新闻走向的观察,非常明显地是在不断扩大。这表现在一些新闻禁区在不断被突破,例如“唐福珍事件”突破了征地拆迁的报道禁区,“三聚氰胺事件”突破了食品安全的报道禁区,“安元鼎事件”突破了截访的报道禁区,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突破了群体性事件的报道禁区。现在除了民族宗教问题和政治异议人士的报道禁区,其他的禁区要么已被突破,要么岌岌可危,许多媒体都在磨刀霍霍。
即使是对政府官员,“李鸿忠夺笔事件”本身就是个巨大的突破,在任的正省部级干部被舆论监督,之前还是很罕见的。而此事之后,省部级干部乃至政治局委员被明确暗示或直接在报道中点名的舆论监督报道,也不少见了。政治局委员,如重庆打黑报道中的薄熙来,《财经》的《公共裙带》中的俞正声。近期《民主与法制》杂志关于陕西榆林赵发琦案的报道,也提到一位由副省长升任省长的干部,此人是谁,读者自然心知肚明。在我看来,可能再过两三年,省部级干部被点名舆论监督的报道,就变得越来越常见。
新闻禁区被不断突破,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新闻“脱敏”。“唐福珍事件”后媒体轰轰烈烈地报道了一年的拆迁,第二年关于征地拆迁的报道就明显减少了,这不是重新发了禁令,而是媒体的新闻判断发生了变化,认为征地拆迁的事件太多,报道价值不大了。几个月前一位同行告诉我,现在拆迁自焚死一个人已经不算新闻,起码要死两个人才算新闻。其他领域也是如此,食品安全问题2011年被轰轰烈烈地报道了一年,明年就会明显减少了,同样是因为“脱敏”而并非“重禁”。
而对上访群体来说,许多上访者认为,媒体不报道他们的事,是因为“不敢”。其实对于上访,媒体历年都有报道,“不敢”的时候已经不多,更多更普遍的是认为新闻价值不够,读者关注度不够。在国外可能是爆炸性的新闻,但在国内因司空见惯,每天都无数次发生,变得没有新闻价值。

其次的话题:中国的新闻自由不断扩大,原因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搞过新闻学研究,所以难以给出比较准确的答案,只能是讲自己的感受,想到多少说多少。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网络技术的日益发达,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尤其是近两三年微博的流行,使得政府的新闻管制能力日趋衰减,客观上扩大了新闻自由。
现在互联网普及的速度太快了,网民的数量曾几何时还在说是三亿,我不知道最新数据室几亿,但一定是极为迅猛地在发展。尤其是网络普及到了农村,现在东、中部地区许多农村都接上了宽带,农民的上网热情很高,不少农村已经是家家有电脑了。网民数量迅猛增加,意味着发帖人数在迅猛增加,从新闻学的角度讲,新闻源头在迅猛增加,政府管制的难度就越来越大了。
如果没有微博,当年“李鸿忠抢笔事件”一定是报道不出来的。那一年的两会,官方还不太知道微博的利害,结果参会记者通过微博搞出了大量的新闻,使得那一年的两会报道新闻跌出,波澜壮阔。而转过年去,官方有准备了,两会报道又变得平稳起来。微博对于新闻报道来说,是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它打通了手机和互联网,使得记者的报道可以瞬时发出,难以管制——这方面本文就不多谈了。
第二,新闻从业人员日渐以招聘制为主,使得旧有的新闻管理体制日渐松动。
现在40岁左右的记者,除了本单位同事外几乎不与其他单位的同行交往;而20多岁的记者,与本单位同事交往不多,反而与同龄的其他单位的同行交往较多。这并非年龄代沟所致,而是20多岁的记者多是招聘制,在本单位有可能朝不保夕,需要时时为跳槽做准备,因而他们为生存计,交往范围自然要扩大到同城媒体圈,而不能局限在本单位了。也因为如此,他们与本单位的关系相对旧体制的记者要疏离得多,新闻管制对他们的影响力就要小得多。
一篇报道,如果被打压,采写的记者被开除——对于完全依附于单位的旧体制的记者,那关乎饭碗,关乎身家性命,往往是他们难以承受之重;而对于招聘制的记者,此处不留爷,爷再找别处,而这篇报道如果因为打压而引起轰动,反而使自己一战成名,对自己今后的从业前途反而增添了砝码,成了大好事。
第三,执政党内部对于新闻报道的尺度总体在向开放方向发展。
伍皓和王旭明都曾是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因为他们都曾做过记者,所以对于新闻和媒体,有自己的认识,也体现在了他们的新闻发言人的职业岗位上。而即使在动车事故中后来被免职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客观地说,他的初衷绝对有主动公开、与媒体友善交往的积极的一面。这三个人的表现可能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而在政府官员中,认为新闻反正已经封锁不了还不如主动开放抢占话语权的人越来越多,新闻报道走向开放的历史趋势,在政府官员中其实是有越来越多的共识。
许多人总是认为,政府的新闻管制有日渐缩进、日渐严密的趋势,所以就觉得新闻被越管越死、新闻越来越不自由,其实是只看到了表面。新闻管制的手段方法的确是在日新月异,办法措施也不断增多,但政府新闻管制的能力是在不断衰减,新闻自由的大趋势是难以阻挡的历史潮流。
许多人近来喜欢提及《新京报》《京华时报》被划归北京市委宣传部管理的事,来说明新闻越来越不自由了。我是不赞同的。谁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头头们就一定会比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官员给予所在媒体更大的自由呢?北京市委宣传部管理着在北京落地的所有网站,他们的尺度如果不是日趋开放,网站的新闻自由空间能够越来越大吗?
其实许多省委、市委宣传部直接管的媒体,反而要比一些党报党刊下属的子媒更自由,因为婆婆离他们的“心理空间”反而远一些。去年一些专家学者、法律人士和媒体同仁共同组织“面粉增白剂”“补铁酱油”“反式脂肪酸”的报道,我也参与其中,亲历其事,报道力度最大的不是《新京报》,不是《京华时报》,反而是《北京晚报》。它的两篇报道,一篇报道题目是《面粉增白剂争论背后是利益与良心的博弈》,一篇报道题目是《补铁酱油,有人在说谎》,从标题就可见其锋芒。认为《北京晚报》天然地就比《新京报》《光明日报》报道力度小,是主观偏见。同样,《民主与法制》有时候的报道力度,比《南方周末》要大得多,当然,《南方周末》做了许多有风骨有担当的报道,令人尊敬。我想说的只是,不具体调查事实,不深入地分析,凭感觉说话,必然判断错误。
在中国,新闻媒体要么是党报党刊,要么是党报党刊下的蛋,都脱离不了党的领导,归谁管还有什么好争的?不论归谁管,报道是否有力,还是要看媒体人本身的政治敏感度和新闻判断力,而上级的管制都是次要的。大多数时候,不是中宣部敏感,不是上级主管单位敏感,而是本单位的领导可能要面临升迁,自己非常敏感,或者那个采写的记者本人就缩手缩脚,先天体质过敏,怎么能全怪上级,全怪中宣部?

话题三:何为新闻效能?
我当初说的是“新闻效力”,后来黎兄学文发微博提及此事时,说的是“新闻效能”,想过之后,我觉得他这个词可能更准确地表达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就采用了。而我能想到的,新闻效能可能包括至少三个方面:一,揭露事实真相;二,推动政府决策和制度变革;三,有助于当事人问题的解决。还有没有其他,欢迎大家补充。
而在上访人员看来,他们找新闻媒体来报道自己的事情,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能够有助于解决自己的问题。好多上访人员会直接问记者:这问题能解决吗?将新闻媒体等同于行政机关、执法机关了。而从“有助于当事人解决问题”的这一新闻效能,在近年来新闻自由不断扩大的同时,是在不断地衰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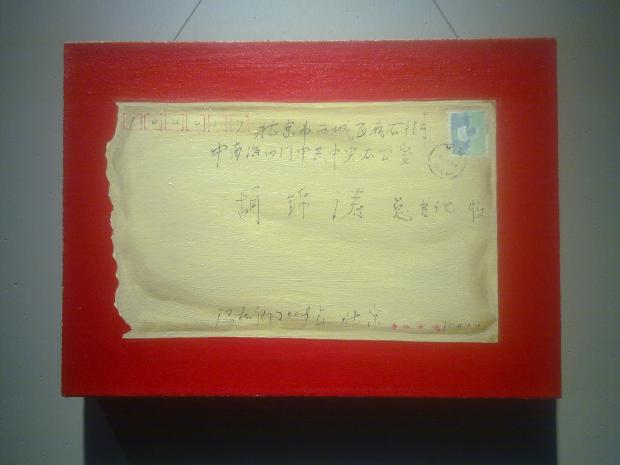
话题四,新闻效能近年来在不断衰减吗?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唐福珍事件。2009年底,唐福珍自焚的视频突然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让媒体人都吃了一惊。听到一个难以证实的传闻,这个视频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来,是某个国家领导人指示的。背景是国务院在推动拆迁条例的修改,但地方政府对此反映强烈,非常抵触。中央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造成舆论压力,压制住地方政府的反弹。于是,唐福珍的视频让全国人民看到了。
2003年以来,因拆迁引起的死亡事件每年都有多起,甚至开发商或拆迁公司都会说一句顺口溜:“拆迁哪有不死人的?”拆迁户的自杀方式,以自焚、上吊、跳楼、割脉为常见。唐福珍事件之前,有关拆迁的报道不是绝对没有,但很少。在山东,有一位地委书记对一位县委书记说:“XX县死了16个人都没事儿,你们县死了一个人就出这么大的事儿!”所谓“出事儿”,就是指被媒体报道了。
而“唐福珍事件”后,2010年是拆迁报道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一年。因为“唐福珍事件”,拆迁的报道禁区被完全突破了。但突破之后,拆迁户的境遇却没有任何改善,所谓“新闻自由扩大,新闻效能衰减”。唐福珍的家属没有因为唐福珍自焚即被广泛报道,多拿到一分钱补偿,唐福珍如果不自焚,还是那么多补偿。而有一位公益律师自费飞到成都呆了一周,想见唐福珍的前夫,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唐福珍的前夫拒不见面。当地政府对唐福珍家属的打压和看管,极为严密,他们的处境比唐福珍自焚前更加恶劣,他们也变得更加胆怯。
参与唐福珍事件整个报道的我的同事王健哀叹:“唐福珍真是白死了。”
也许,对于揭露真相和推动拆迁条例的修改,唐福珍自焚有一定的意义,但在一条鲜活的生命面前,这样的意义太残忍了,对死者太没有人道了。
在新闻禁区日渐突破的同时,地方政府的脸皮确实是越来越厚了,他们对付新闻的办法和手段也越来越“纯熟”了。
当时《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著名揭黑记者王克勤,那年与我偶遇,我记得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老师请我们的一次聚会。他对我说,目前拆迁报道的态势是,媒体与市、区、县地方政府已经展开了攻防战,地方政府应对媒体的办法主要有四种。
一是冷处理。你报你的,我拆我的,充耳不闻,只当你的报道不存在,加快拆迁步伐,将拆迁进行到底。唐福珍自焚事件后,金牛区区长马旭所作的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只字未提举国关注的唐福珍事件,却把旧城改造和重大项目拆迁“签订拆迁协议6757户、企业184家”作为成绩进行报告。
二是热处理。你报我拆迁不好,我也组织一批媒体,报道我的城市化进程有多好,棚户区改造有多好,人民群众多么支持拥护。如发生过自焚事件的黑龙江省东宁县,当地媒体大张旗鼓地报道县长任侃率县政府考察团赴吉林、辽宁考察学习城市建设、棚户区改造,被考察城市“对拒不拆迁的被拆迁户,各地均采取了依法行政强迁,在拆迁中改造了城市,在拆迁中消除了烟尘污染,在拆迁中改善了百姓的居住环境,最终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大家纷纷表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我县棚户区追赶、跨越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三是硬处理。如广西荔浦警方在2010年年初曾跟踪来当地报道征地拆迁事件的新华社《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跟踪几天后在广西阳朔县将其拘传,押上警车带回荔浦,引发一场风波,后将记者释放。
四是软处理。一些政府官员利用各种渠道各种关系,找到媒体领导或媒体的上级主管单位,做工作,施加压力,再送上广告费、发行费,最终成功撤稿。
王克勤认为,这四种处理方法中,冷处理是最常见的,热处理也时有发生,而硬处理是最“傻”的,软处理则是最“有效”的,也是最狠的。
新闻效能的衰减,应该有个纵向比较。就以王克勤为例,2002年初,他的一篇《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的报道,导致大批官员锒铛入狱。那一年,先后有168人因他的报道被送进监狱。而到了去年,山西疫苗案的报道比当年的报道引起更大的轰动,但有没有一名官员因为报道哪怕是受个最小的处分呢?没有。
事实胜于雄辩。不管你去问哪一个有几年从业经验的调查记者,他们都有这样的感受。新闻自由是在扩大,但政府官员越来越不在乎新闻报道了,这是事实。就以去年的一些公共事件为例,河南杨金德案不可谓不轰动,但基本无效能。北海案不可谓报道得不多,但当地公检法的态度依然暴戾。动车事故,原因至今不明。郭美美事件后,慈善立法并没有推动。
当然,新闻效能的衰减,也不是全方位地。像校车事故,新闻报道就能起到明显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财政拨款买点校车比较简单,改善的成本较低,不出动地方政府的根本利益,也不触及制度变革。还有像微博开房、微博调情这些官员的桃色新闻,处理起来还是蛮快的。而一旦触及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和基本制度,还有贪污腐败问题,新闻效能的衰减就极为明显。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谈了。

话题五,新闻自由扩大而新闻效能同步衰减的原因何在?
原因也很简单。这是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新闻舆论要想起到解决问题的作用,那就一定要进入党政权力体系。也就是说,只有当某个单位某个官员的上级党政机关或党政领导,对新闻舆论做出了批示,新闻舆论才能起作用。而随着新闻自由的不断扩大,各种问题被曝光得越来越频繁,各级党政官员的羞耻感就被磨练得越来越坚实,他们也越来越懒得对新闻舆论做出回应了。
对于上访群体来说,新闻媒体不报道上访事件,通常不再是不敢,而是觉得没有新闻价值,不愿。而即使报道了,对于解决上访者的具体问题,也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新闻自由的扩大与新闻效能的衰减,的确是同步的,而长此以往导致的政治后果和社会影响,就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本文也已经很长,到此打住吧。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